来源标题:《人世间》:那被我们“进化”掉的善良与恻隐
根据梁晓声茅盾文学奖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年代剧《人世间》,伴着农历新年的到来,给国产电视剧确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开端,俨然成为继《父母爱情》《金婚》等现象级年代剧之后的又一个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高点。映衬着中国最具烟火气的春节,剧中周家兄妹和光字片邻里的故事,也被印染上了一种只有中国人才懂的情结和底色。
尽管剧中设定的时间线和大背景明确含有三线建设、知青下乡、改革开放等历史际遇和话题,但很明显,电视剧改编最大程度追随和尊重了小说创作的本意。人物和故事始终是主体,这也是接近的时代背景下,《人世间》和《大江大河》等作品有着明显不同气质的根本原因。电视剧很好地完成了梁晓声在文学创作上对“他者”的观照,存留了年代剧最容易缺失、也是最珍贵的拙朴。
我们的骨子里都住过一个周秉昆
剧中的周家三兄妹,每个人都能代表那个特定年代的一个群体。在这样的大部头作品里,被投入笔墨最多的主人公,既不是乘风破浪的有志青年周秉义,也不是个性自由、思想独立、充满话题感的周蓉,而是只有初中文化程度、向来被全家人“笑话”的周秉昆。他身上的青楞、憨厚、耿直、毛糙、“行就行,不行就拉倒”的率性是我们身边最常见到、也最容易找到的人,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。但在生活的课堂里,我们努力的目标恰恰都是:要成为比周秉昆更“优秀”的人。所以我们对周秉昆的心疼,也正是对那个还没有完成“进化”的自己的疼惜。
如果说一部作品只能由一个人物代言,来完成创作者的精神传递,那么在《人世间》里的这个代言人只能是周秉昆。在他作为光字片区小老百姓的酸甜苦辣、风雨波折的人生历程中,始终没有褪色的是人性中最柔软和善良的那部分,所以他才在年轻时不畏人言,一心喜欢“有污点”的郑娟,对待老弱幼饱含仁爱之心;他才会在万难中让好友国庆一家搬出周家老宅时,却觉心中有愧,抱头痛哭;在法庭上,相比刑期长短,郑娟自曝被强奸的身前事,让他对无法保护心爱之人的名声更感无力和绝望……如此种种,皆是周秉昆身上始终不变的恻隐。而这份善良,不单单在周秉昆一个人身上,在整个光字片区的乡里乡亲身上,因时因地因事,我们都不难发现他们的善意。这份平凡与实在,是整个社会最大面积也最基础的构成。我们的骨子里都住着一个周秉昆——只是有人最终努力走出了光字片区,成为了周蓉和周秉义,或者成为了骆士宾和水自流,又或者始终没有走出,住在老宅里,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迎击生活的磨砺,哭着笑,笑着哭。从小说到电视剧,都尽可能保持了平视视角,安静地记叙岁月,也极大拉近了观众和作品的距离。
比起早年间《大哥》《大姐》《大嫂》等同类年代剧中,突出表现勇担生活之苦、百般磨砺仍笑对一切、甘愿牺牲自我成就他人、绝对占据精神道德高地、让人心生敬意但却望而生畏的小人物中的“大英雄”们,周秉昆在《人世间》里的付出、挣扎和奉献都去掉了神圣感和救世主的影子,真实而可亲。
已经远去却令人怀念的时代
除了人物本身,《人世间》里白描的诸多光字片区的平头老百姓,共同构筑了那个特定年代的中国底层社会的人际关系:零边界感。以周秉昆为首的“六君子”群体,绝对是那个历史时代年轻人关系交往的最典型写照:有难同当,有福同享,即便各自组建了家庭,但一个个小家庭之间也可以做到没有围墙,没有秘密。这是物质匮乏时代下,让人团结互助的一种必然与客观,也是中国社会民众还没有精神独立、个性自由还未蔚然成风之际,很长一段时间里人际关系的普遍特质。在物质生活上,人们需要互相依存才能更好地生活;在精神生活上,人群聚拢是传递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。
在水泥墙高耸、一人一个门洞、一个手机一个世界的今天,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非血缘的社会关系对于中年观众来说,是一次无助的、深切怀念又都回不去的深情凝望;对于年轻一代观众而言,则是一次新型交际关系的猎奇,亦是一种无法在当今社会环境土壤中复制的遗憾。彼时的《人世间》虽已非此“人世间”,但却丝毫不影响我们穿越代际,产生对人生、生活的理解和共鸣:甘苦的表现形式和内容虽已不同,但我们始终都想方设法、生生不息地把岁月趟过去。
梁晓声在《人世间》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有这样一句话:“我认为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,文学对文化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,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……”显然,电视剧《人世间》已完成了这场从文学到影视剧的接力,小说中那群有情有义、勇担生活之责的小人物已在电视荧屏上,给这个时代下的万家灯火中,注入任由人生坎坷、“我不啼哭,不哀叹,不悔恨”的坚韧生长之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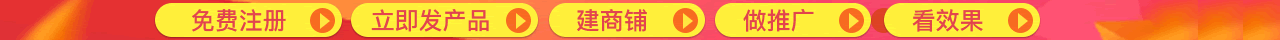
《人世间》:那被我们“进化”掉的善良与恻隐
来源:北京日报 浏览次数:188次 发布时间:2022-03-05
- 上一篇: “周秉昆”雷佳音:这个角色让我更懂得珍惜生活
- 下一篇: 5G是否意味着WiFi的终结
相关文章
- 2026-02-13全网都知道你娶到了李婷!这场“婚礼”看哭网友
- 2026-02-13上海一保姆盗窃雇主价值30多万的名牌首饰等,变卖了13万元!警方介入→
- 2026-02-12米其林PS5轮胎的湿地制动性能如何?
- 2026-02-12米其林PRIMACY SUV+轮胎的耐磨指数是多少?
- 2023-10-092024年绵阳市高考报名入口www.zszk.net
- 2023-10-092024年黑龙江省高考网上报名gkbm.hljea.org.cn:8003/hljzkbbm
- 2023-10-092024年福建省高考网上报名gk.eeafj.cn或www.eeafj.cn/sygkgzyy
- 2023-10-092023陕西省全国计算机应用水平考试网上报名http://nit.neea.edu.cn
- 2023-09-22大泽湖·海归小镇研发中心(一期)项目鸟瞰效果图 施工进展图
- 2023-09-22为何要建设海归小镇?大泽湖·海归小镇具体怎样建?
最新收录


 北京芷衡律师事务所官网
北京芷衡律师事务所官网 号令天下
号令天下 V-Next 深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
V-Next 深交所创新创业投融资服务平台 创业邦 - 关注创新经济及其推动者
创业邦 - 关注创新经济及其推动者 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
达晨财智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百度作家平台-一站式AI小说创作与投稿平台
百度作家平台-一站式AI小说创作与投稿平台 茶杯虎 - 发现好电影,分享新乐趣
茶杯虎 - 发现好电影,分享新乐趣 豌豆PRO-全网影视聚合搜索
豌豆PRO-全网影视聚合搜索 许搜 - 网盘资源搜索神器
许搜 - 网盘资源搜索神器 可乐影视
可乐影视 嘉科网络
嘉科网络 金点子
金点子